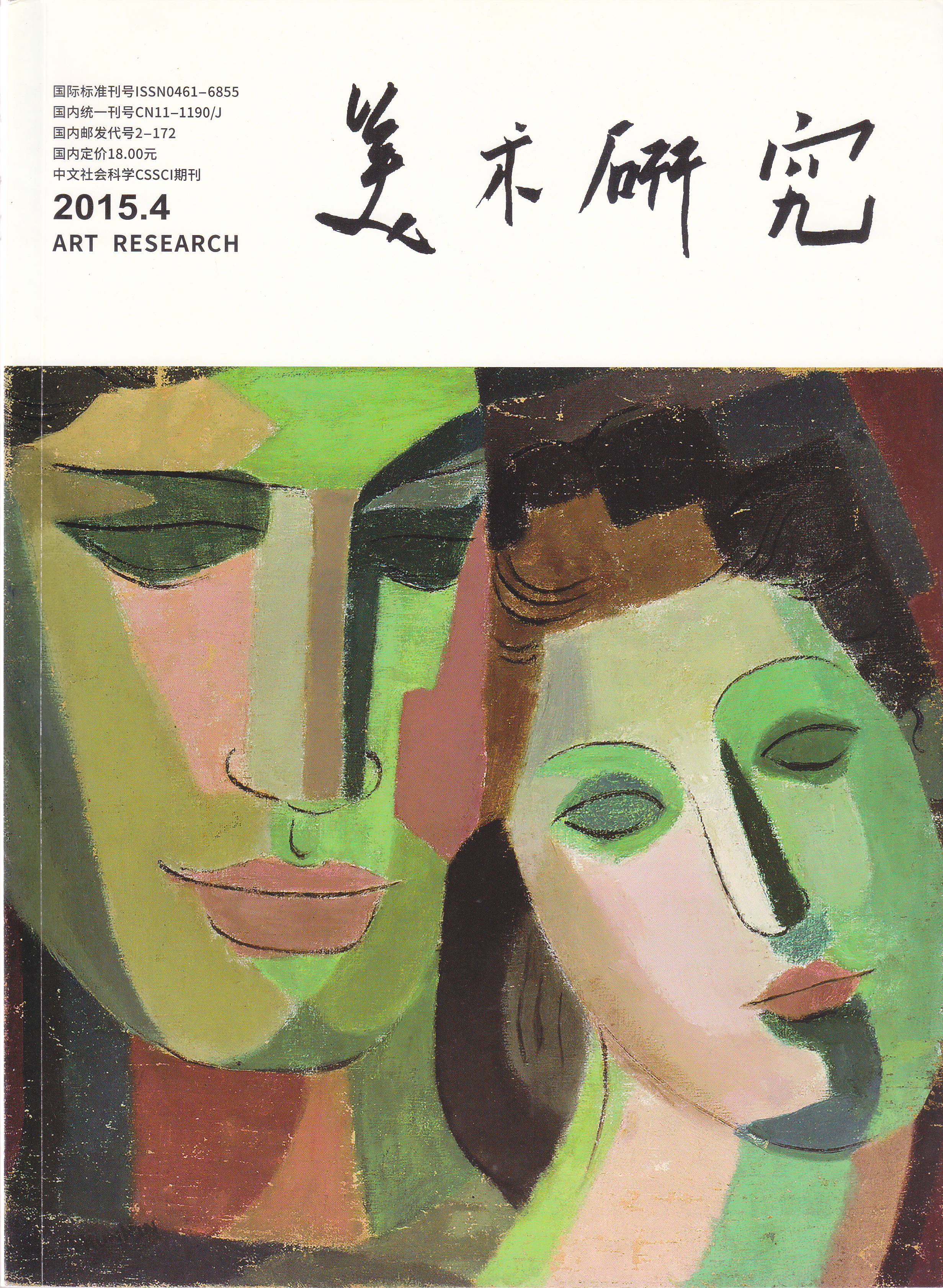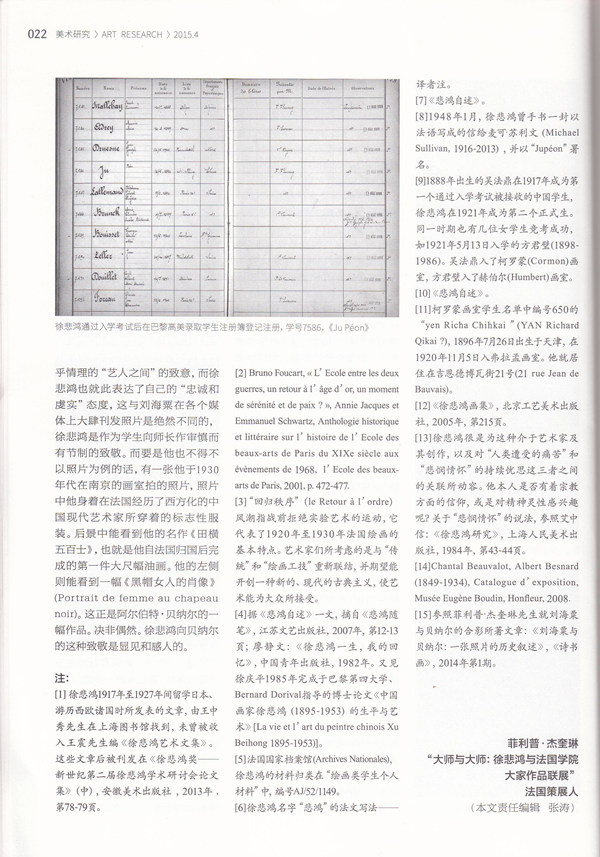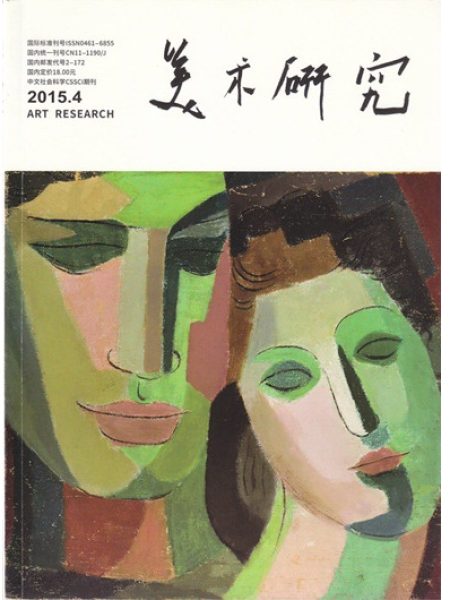菲利普·杰奎琳(Philippe Cinquini),《徐悲鸿和他的法国老师们:一段杰出的艺术历程》,载于《美术研究》,2015年第4期,第15-22页。
摘要:
徐悲鸿在1922年10月30日写了一篇关于雷恩·波纳 (Léon Bonnat, 1833-1922) 的文章。两个月后,他继续就法国艺术写了一篇评论,其中提到的是当时任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院长的阿尔伯特·贝纳尔(Albert Besnard, 1849-1934) 。文章以 “新闻式的语言”阐示了徐悲鸿对贝纳尔以及法国艺术的赏鉴。籍此,十年之后徐悲鸿为巴黎的中国艺术展事宜而返回巴黎时又与贝纳尔有所交往,也就不令人吃惊了。徐悲鸿请他为展出写序,但贝纳尔因为身体欠佳,转而向他推荐自己的朋友,作家和法兰西学院院士保罗·瓦莱里 (Paul Valéry, 1871-1945) 来作序。
自1922年起,徐悲鸿就对贝纳尔的生平和艺术创作多有关注。他亲自欣赏过这位艺术家的创作,并写有情感充沛的评论:“先生为世界最大画师之一,当代印象派巨子,其艺以柔曼郁妙胜,用笔虚和婉转,古今所未见也。”文中他也提及自己与贝纳尔的心有灵犀:“吾于法之倍难尔,无间然矣。”就像预先有所计划那样,徐悲鸿选择了自己的立场:法国学院派艺术,是十九世纪“大艺术”(Grand Art) 的一种继承。
关于贝纳尔的这些评述文字让我们能以全新的方式来看待徐悲鸿在回国后的1920年代末至1940年期间完成的一些大作品。在对一些曾引发其法国老师长久思索的问题再度探询时,徐悲鸿无法回避的是在“历史画”和“大幅装饰画”之间所存有的特殊关系。在他1922年的文章中,他特别提到曾前往欣赏过的贝纳尔为巴黎市政厅完成的天顶画原作,徐悲鸿对贝纳尔这幅绘画科学主题的作品中“大气恢宏的构图”很是钦慕:完全没有历史要素,而是托寓、梦幻和装饰性的创作。诚然,徐悲鸿因为时局环境所限而未在中国创作过大幅装饰画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九方皋》以及其他一些大幅作品,都带有着巨幅装饰画 (monumental et décoratif) 的特征。这一审视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徐悲鸿留法经历中未曾被探讨的一部分,以及他在其中获得的艺术训导。而徐悲鸿也知道,在贝纳尔、弗拉孟或柯罗蒙这些老师身后,隐约显现的是皮埃·普维·德·夏凡纳 (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 1824-1898) 的炫彩阴影,这位艺术家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年轻法国艺术家施有重要的影响。进一步举例说,如今参观北京国家博物馆时,能看到徐悲鸿作品《愚公移山》的一件大尺幅的浅浮雕。尽管这一摹本并不细致,但从中能看出徐悲鸿以油笔和墨笔两种技法完成于印度的这件作品所具有的大气和装饰属性 。徐悲鸿与法国大幅装饰画的这种关联性部分地抵消了学界对于他作品中所谓历史画特征的批评性论述。而撇开他与东方绘画的根系渊源不谈,我们从绘画形式的角度进一步说,即便徐悲鸿所画的不是“西式的大幅历史画”,他似乎也是倾向于绘画一些供博物馆参观的大幅、带有历史属性的装饰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