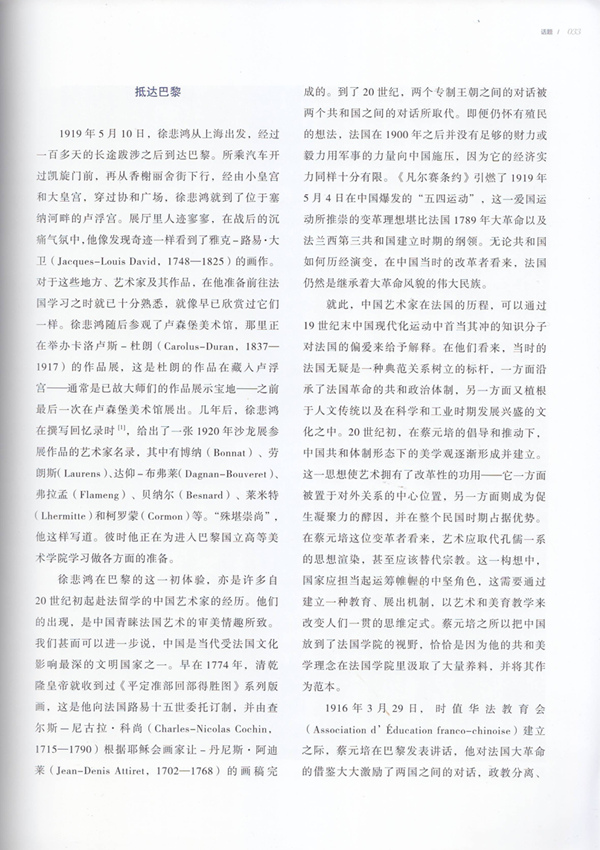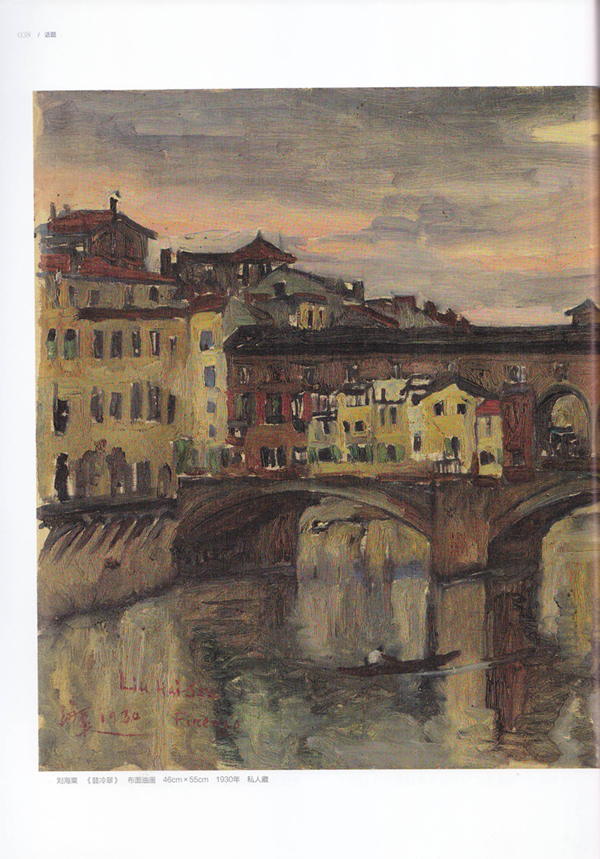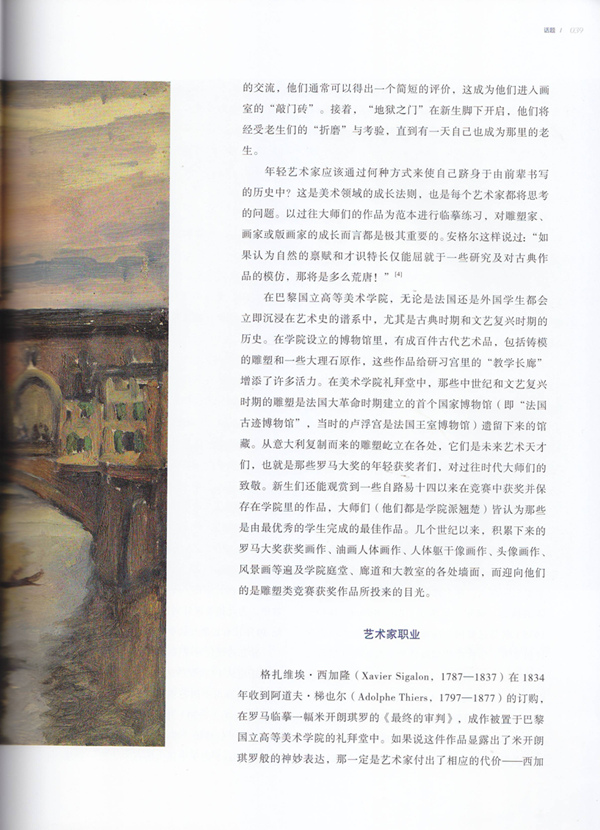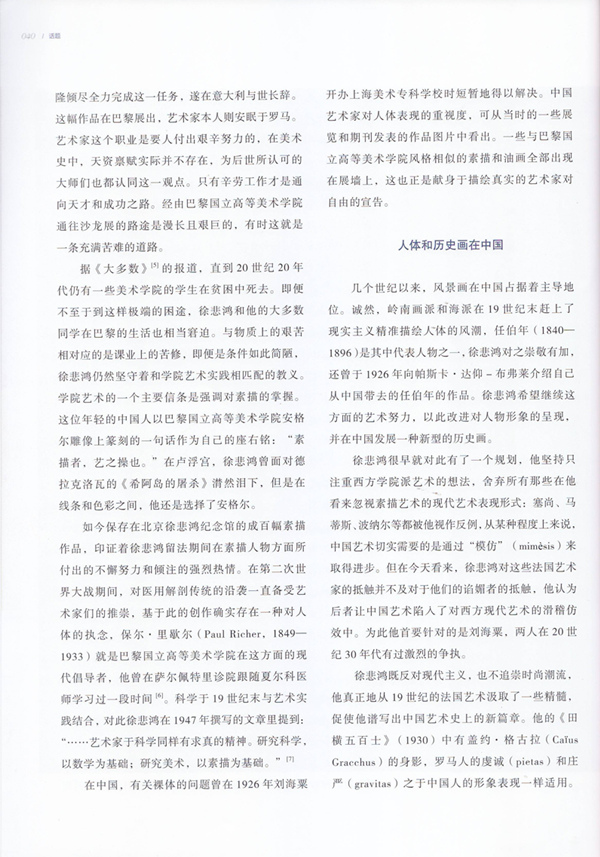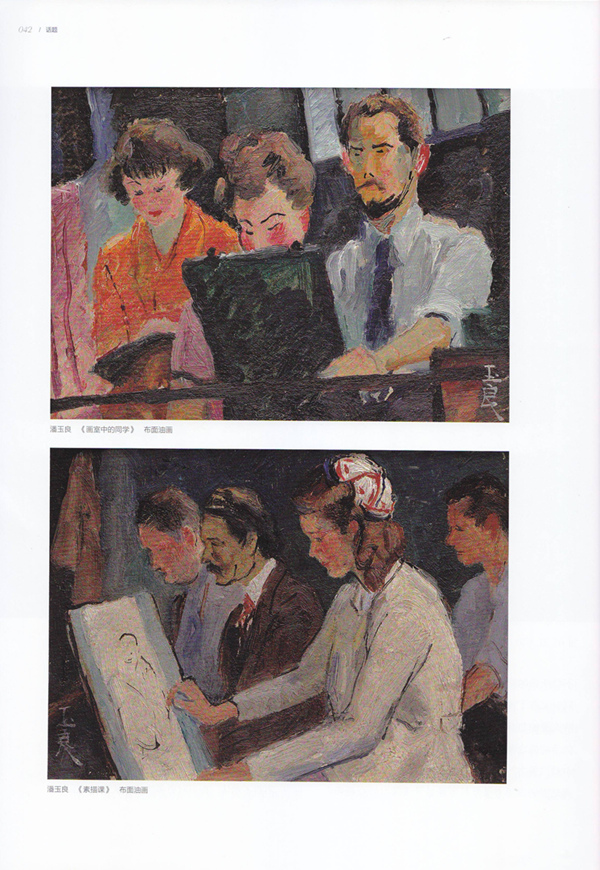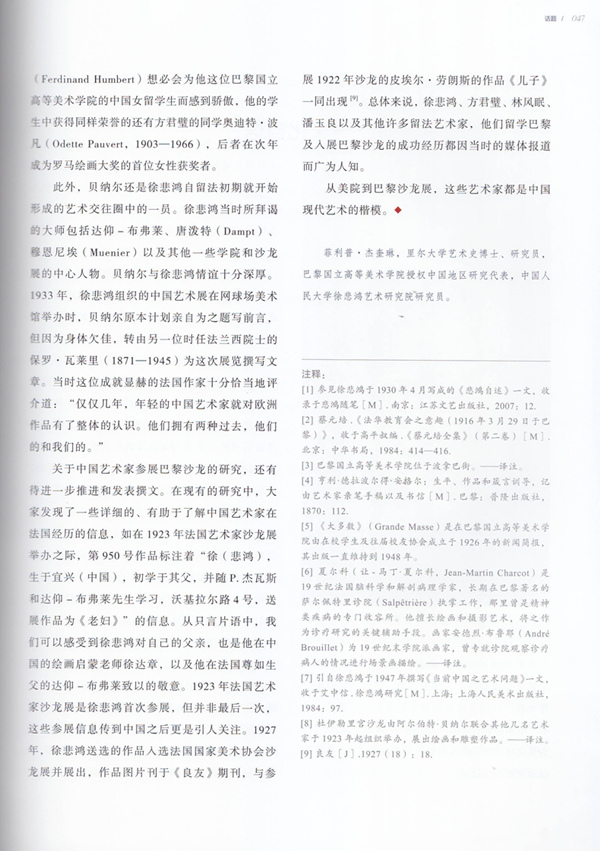菲利普·杰奎琳(Philippe Cinquini),《一个美术的梦——从巴黎到北京》,载于《油画》,2018年第1期,第32-47页。
摘要:
1919年5月10日,徐悲鸿在从上海到欧洲长途跋涉了100多天之后到达巴黎。所乘汽车开过凯旋门前,再从香榭丽舍街下行,经由小皇宫和大皇宫,穿过协和广场后到了塞纳河岸。徐悲鸿就这样来到了卢浮宫。展厅里人迹寥寥,在战后的沉痛气氛中,他像发现奇迹一样看到了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的画作。对于这些地方、英雄人物和作品,在他准备前往法国学习之时就已十分熟悉,就像早已欣赏过它们一样。徐悲鸿随后参观了卢森堡美术馆,那里正在举办卡洛卢斯-杜朗(Carolus-Duran,1837—1917)的作品展,杜朗的作品是在藏入卢浮宫—通常是已故大师们的作品展示宝地—之前最后一次在那里展出。几年以后,撰写回忆录时,徐悲鸿给出了一张1920年沙龙展参展作品的艺术家名录:博纳(Bonnat)、劳朗斯(Laurens)、达仰-布弗莱(Dagnan-Bouveret)、弗拉孟(Flameng)、贝纳尔(Besnard)、莱米特(Lhermitte)和柯罗蒙(Cormon)等。“殊堪崇尚”,他这样写道,彼时他正在为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巴黎高美)学习做各方面的准备。
徐悲鸿在巴黎的这一初体验,许多于1910年代起赴法留学的中国艺术家有同样的经历。他们的出现,是中国青睐法国艺术的特别审美情趣所致。我们甚而可以进一步说,中国是当代受法国文化影响最深的文明国家之一。早前,乾隆皇帝在1774年就收到过他向路易十五世委托订制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系列版画:由查尔斯-尼古拉·科尚(Charles-Nicolas Cochin,1715-1790)根据耶稣会画家让-丹尼斯·阿迪莱(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的画稿完成。到了20世纪,两个专制王朝之间的对话被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对话所取代。即便仍怀有殖民的想法,法国在1900年之后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或毅力来以军事力量向中国施压,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同样十分有限。《凡尔赛条约》引燃了1919年5月4日的事件,这一中国革命运动所推崇的变革理想堪比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时期的纲领。无论共和国如何历经演变,在中国改革者看来,法国仍然是继承着大革命风貌的伟大民族。
就此,中国艺术家在法国的历程,可以通过19世纪末、中国现代化运动中首当其冲的知识分子们对法国的偏爱来给予解释。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无疑就是一种典范关系树立的标杆,一方面沿承了法国革命的共和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又植根于人文传统以及在科学和工业时期发展兴盛的文化之中。在1910年代,蔡元培确立形成了中国共和体制形态下的美学观。这一思想使艺术拥有了改革性的功用,并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占据优势。如此境况下的艺术就被视作一种变革力量;它被置于对外关系的中心位置,于内则成为促生凝聚力的酵因。对这位变革者而言,艺术应取代孔儒一系的思想渲染,甚至应该替代宗教。这一构想中,国家确应担当起运筹帷幄的中坚角色,这需要通过建立一种教育、展出机制,以艺术和美育教学来改变人们一贯的思维定式。蔡元培之所以把中国放到了法国学院的视野,恰恰是因为他的共和美学理念在法国学院里大量汲取了作为范本的养料。